我們問了13個大學生:為什么要講脫口秀
作者:陳宇龍 樊星 黃曉穎 蔣肖斌
發布時間:2025-04-11 21:47:36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4年11月29日,南大心理中心舉辦“一南一度”心理脫口秀專場。受訪者供圖
他們試圖在大學生活里開辟績點、實習等“軌道”之外的另一番天地。
劇場里的觀眾需要費一些功夫,才能察覺到舞臺上這個名叫王陽元的年輕人和其他脫口秀演員有些不同。去年,他跑了300多場“開放麥”,人們在這個提供給演員們練習、打磨段子的場合遇到他的概率不小。勤奮的訓練讓他即使有時語速飛快,也常常是一場演出里收獲笑聲最多的演員之一。
不同職業的人在工作日的夜晚,一頭扎進北京的胡同里,他們通過一支拖著長線的麥克風,和臺下的觀眾共享一些類似的煩惱:被催婚、加班、職場關系復雜……王陽元則會先說明自己的學生身份,再聊家庭、初中和大學的故事,必要時,他會介紹自己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在舞臺上,他自稱“艾斯”,是日本漫畫《航海王》里的一個角色名。
艾斯在學校社團認識的好友小魚(余東俠)2024年登上了一檔脫口秀綜藝,讓大學生演員走入了線上觀眾的視野。2024年,脫口秀這個藝術形式收獲了超乎以往的熱度。離開節目后,小魚的演出最多排到一個月18場,每周末,他在上海、香港等不同城市講段子,這是他從未體驗過的生活。
大學生是脫口秀綜藝舞臺上的稀缺人設,網友們嘆服小魚“3次高考總計1900分”段子的精妙,但也調侃他何以緊張得手臂反復舉起、放下,就像“不知道該怎么安放的雨刮器”。節目主持人發現他始終在講和學習相關的段子,只是分了不同階段,他心想:我還能講什么呢?不過,從收到的反饋來看,舞臺上的無所適從與未能褪去的青澀,連同校園話題,都被觀眾一一接納。
一段時間以來,更多像小魚這樣的大學生創立脫口秀社團或走出校園演出,有時一場10人的“開放麥”能有3名大學生演員登臺。他們在舞臺上替人化解負面情緒,希望用真誠贏得笑聲,也試圖在大學生活里開辟績點、實習等“軌道”之外的另一番天地。他們中的少數人借此擁有了可以緩解經濟壓力的副業,但更多人只享有瞬息的“聚光燈時刻”。
回到現實,脫口秀為他們的人生留下了什么?
做這件事,本身能不能獲得快樂
1月6日,周一的晚上,北京王府井一家商場的地下一層,單立人劇場的舞臺下擺了一圈椅子。直到觀眾坐下的那一刻,演出還是充滿神秘。這是一場由趣聽喜劇舉辦的“盲盒專場內測”。對于脫口秀演員來說,舉辦個人專場演出是“成熟”的象征,意味著他擁有持續講60分鐘以上的能力和段子儲備。
“(專場)和其他的脫口秀表演不一樣,我們可以充分了解這個演員的段子內容和內心世界。”主持人在臺上說,“為什么叫‘內測’呢?顯然這個東西就是‘不好笑’。”他解釋,這是演員第一次呈現這個作品,來測試時長和觀眾的接受程度,同時希望大家降低預期。
中國香港演員黃子華在1990年引進這種名為“Stand-up Comedy”的表演形式時,中文世界還沒有它的任何譯名,他為其起名為“棟篤笑”。在之后的本土發展中,“單口喜劇”被認為是最恰當的翻譯,但“脫口秀”的說法流傳更廣。無論用哪個名字,它都仍然是小眾藝術。每次演出時,主持人都會請第一次看線下演出的觀眾鼓掌示意,每回都有半數以上的人是初來乍到。看這場演出的觀眾,有的是考研結束來商場吃飯,順便買了一張票。
舞臺幕后,這場演出的“主咖”、等待登臺的艾斯緊張得冒汗。一小時前,他在粉絲群里丟下一句“去背詞了,真記不住”,就消失了。
對于講了兩年半的艾斯來說,脫口秀幾乎和讀研生活同步。考研復習時他就想,讀研后要做些不那么功利但有意思的事情。他有很強的“人生意義焦慮感”,“評價是否喜歡一件事情的標準,是做這件事本身能不能獲得快樂。實習、考試都是需要獲得那個結果才能快樂,考不上我就不快樂”。
這些大學里的脫口秀愛好者有著類似的心跡,暫時困在人生新階段的入口,卻也逼著他們向前邁出許多步子。濟南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專業學生李昕悅對高考結果一直不滿意,她曾在山東一所很好的高中讀書,心理落差很大,但總找不到突破口。直到看了一次“開放麥”演出后,她決定把高考經歷寫成段子,“當時就覺得有機會一定要嘗試一下”。
2022年下半年,艾斯還沒有正經看過線下脫口秀演出。他花兩三周時間琢磨出一篇吐槽地鐵擁擠的稿子,投給很多家脫口秀廠牌,獲得了一個上臺機會。第一次演出,臺下只有零星的笑聲,但結束后他就被拉進了正式演員的報名群。“開放麥”不帶來任何收益,他卻跑得越來越勤,白天上課、實習結束后趕到劇場,還要在幾家廠牌之間趕場,兩年來晝夜忙碌。
一個業余演員從積累段子到推出第一個專場只用兩年半是一個比較快的速度。段子之外,艾斯還通過“開放麥”和近期的幾場商業演出積累了一定人氣。在內測專場現場,一名北京林業大學的學生告訴記者,艾斯是她最喜歡的演員,“可能因為他太勤奮了”。她經常和朋友來看演出緩解科研壓力,雖然已經聽過艾斯在專場里提到的全部段子,但串聯起來還是覺得很好笑。
“過飽和狀態”中,一個釋放壓力、尋找自我的出口
講了3個月,艾斯才知道,北大有個“學生趣聽脫口秀協會”(以下簡稱“趣聽”),他終于有個地方能和人交流關于脫口秀的事了。社團里,碩博生比本科生要多,“可能是碩博生壓力更大一點”。他和本科生小魚、謝謝(謝淇汀)成了好朋友,2023年,3人經常一起報名“開放麥”,互相提建議,一起改段子。
小魚是社團創始人之一。回頭看,他認為自己最初上臺也是因為意義感缺失,失去了生活的“秩序”。作為一名縣城中學的尖子生,他在北大校園里遇到了“真正意義上的學霸”,也逐漸意識到“成績”不是唯一評價維度。學習之外的能力、創造實際價值,他想在脫口秀中探索這些。
這種探索和改變自己的強大意愿,在很多登臺的大學生身上都能窺見。演員船長(藝名)很早就發現,自己和身邊人的想法不太一樣,同學們按部就班、很少說“不”,早早定下的目標是擁有一份高薪工作,生活節奏和社會時鐘的齒輪緊緊咬合。
船長不喜歡這樣的生活。2021年,在北京郵電大學讀書的他帶著高中時期的綽號站上了脫口秀的舞臺。小時候,他就喜歡表演,在學校的節目中,他演過13分鐘的烏龜,也演過把嘴唇涂成藍色的惡魔,目的都是逗人笑。在他看來,“逗別人笑是件很好的事情”。
那時北京的脫口秀演員還不太多,新人只要向廠牌報名就能上場。但一連幾次演出,場子都很“冷”。不過因為人不多,演員們會聚在一起,互相幫忙改段子。他發現自己的社交圈子,比待在校園里的同學更豐富。
3月2日,北京市東城區的南陽共享際劇場里,今年24歲的船長小跑上臺,接過麥克風。在全場人的目光中,這名通信工程專業的研究生聊起學業和生活。年輕的苦惱來源于很多方面,比如對學術研究的“幻滅”、對學歷“內卷”的不理解、追求喜歡的女生被拒絕……在45分鐘的表演中,臺下不時響起笑聲和掌聲。
南京師范大學研一學生陳一是導師的“開山弟子”,生活總是被科研填滿。在充滿公式、數據與代碼的日常里,他覺得講脫口秀不是單純的愛好,而是他“過飽和狀態”中的一個釋放壓力、尋找自我的重要出口。
上臺的新人或早或晚都會意識到,自己的負面情緒是上臺的動力,同時也是創作的“富礦”:吐槽生活中的瑣事、煩惱,將之轉化為笑料。一名學生演員直言,喜劇的創作邏輯就是在糟糕的生活里找點“好玩的東西”。
在趣聽,艾斯發現,一些人上臺是“一次性”的,只是為了吐槽生活里不愉快的事情,“說完就走了”;另一些人會把社團當成學習之外的一個歸屬地,周末來“講個段子,玩一玩”。艾斯能堅持下來的直接原因是,他享受把有意思的想法寫成段子,吐槽可以是一種創造方式,但不能成為驅動力。

艾斯在趣聽喜劇廠牌演出。 陳宇龍/攝
艾斯希望能在演出里和觀眾實現情感共鳴,建立某種“連接”。“他能夠理解我當時真誠的想法,而不是只站在一個看演出的角度,覺得這個東西好笑。”
第一次登臺,觀眾的眼神從期待、迷茫再到失望
在獲得觀眾最真實的身體反饋——“笑”之前,學會接受冷場是脫口秀新人的必修課。校內的“開放麥”上演得效果再好的段子,拿到校外,都可能會迎上一盆冷水。
2023年4月,讀本科的孟軒在蘭州的甘肅大劇院第一次觀看脫口秀線下演出,她仿佛被一種魔力牽引,心里冒出一個聲音:“我也想站上那個舞臺。”在南京師范大學讀研后,她終于有了演出機會。然而,站上臺的一瞬間,孟軒的腦海中充斥著難以抑制的慌亂。盡管沒有忘詞,但觀眾的冷淡反應讓她倍感失落。“他們的眼神從期待、迷茫再到失望。”她的心也隨之跌入谷底。
講脫口秀的0次到無數次之間,還有最難越過的“第一次”——第一次講碰到冷場,足以“勸退”很多人。
那次挫敗讓孟軒意識到,作為學生演員,她與觀眾的生活經歷不同,笑點自然難以完全契合。圍繞宿舍關系寫的段子,在首次演出中“敗陣”,成為她脫口秀生涯的開端,也是截至目前唯一的嘗試。
講過500場以上“開放麥”的船長知道,觀眾的年齡是一場演出里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之一,但這是他決定不了的事。他記得一位已經結婚的前輩在演出時講帶娃的段子,臺下的觀眾看起來都不到25歲,“完全沒領會”。
“什么樣的段子匹配什么樣的觀眾”,對他自己來說,只有部分人能理解研究生生活的話題。
3月2日的南陽共享際劇場,現場觀眾不到百人,大部分是不到30歲的年輕面孔。北京室外的溫度仍是個位數,船長卻穿著短袖,額頭不時滾落汗珠。上臺前,他在門外的走廊里轉了好幾個圈。
演出過程中,有幾處調侃研究生學業的梗,效果不算太好。一名坐在第一排的觀眾突然起身,在劇場中接起電話,兩人的聲音交錯在舞臺上空。船長稍稍加大了音量,但這場注意力“搶奪戰”只持續了半分鐘左右,船長主動給表演“按下暫停鍵”,示意等觀眾接完電話再繼續。
不過,后面的大部分梗都“響”了。有觀眾認為這場演出“提供了很好的年輕人觀察視角”,同時覺得,臺上這個年輕人的煩惱背后涉及龐大的社會系統,很難通過成長或是講述被解決。船長不會提前考慮這些,經過他反復打磨、試驗后留下來的段子,組合在一起,“反過來促成了他的表達”,而他繼續講下去的原則,仍然是“先逗大家笑吧”。在他看來,能夠逗笑別人,給別人帶去快樂,“難道不好嗎?”

即使在冬天,船長每次演出都只穿T恤。受訪者供圖
李昕悅也遇到過冷場的時刻,她準備的追星段子,在“開放麥”試了好幾次,效果都不好。但她不認為這是話題本身的局限,“我記得有一個前輩,他是足球解說員,他的段子內容都是圍繞足球,這也是一個小眾的領域,但他就是講得很好笑,我覺得還是方法上的問題”。
這名大二學生在脫口秀里收獲了友情。2024年跨年夜,她在劇場演出,晚上和一群脫口秀演員一起跨年,因為脫口秀,“一群朋友在一起”,讓她覺得很溫暖。
廣州大學的大一學生王境珊高考結束就想試著講“開放麥”,在家鄉廣東揭陽找不到廠牌,她就坐兩個小時車,“跋山涉水”地到汕頭去演。
開學后的一天傍晚,她坐公交車去劇場講“開放麥”,窗外閃過正在散步的一家人。她突然想到了自己,一個人在廣州上學,一個人坐一個多小時車從學校到劇場,公交晃得她發暈,而接下來,還有令她緊張的演出。身體和心理的疲憊擊中了她,那一刻,她覺得很難過,眼淚快要掉下來。但演出結束后,這種感覺消失了。
那天演出,臺下不時傳來觀眾的笑聲,結束之后,演員聚在一起聊天,有演員鼓勵她,多練習就能講得越來越好。王境珊從小就在意別人的評價,這一點小小的鼓勵,足夠她開心很久。她想,這大概也是自己喜歡脫口秀的一個原因:講出來,立馬就能得到反饋。
講了100多次“開放麥”后,父母第一次來看他演出
小魚正在經歷第二次“失序”。獲得更多關注和演出機會之后,他忙到“混亂”,一邊是畢業論文開題的壓力,一邊是害怕失去已有的機會,他“被各種事情推著走”。

小魚在北京大學學生趣聽脫口秀協會演出。受訪者供圖
另一個焦慮是“很久寫不出段子了”。在綜藝節目里,他講的都是對他的人生影響非常重大的事情。節目第一輪,他講的是自己的專業預防醫學,對于第一次在視頻平臺亮相的他來說,這算得上是一次正式的自我介紹。第二輪,強勁對手帶來的壓力和大學幾年的緩解,讓他有勇氣去講述自己復讀兩次的故事。他一直有“復讀羞恥”情緒,朋友謝謝認識他兩年,也是在節目錄制前才知道這段經歷。
“別人問我高考多少分,我說:哼,1900。”這是經典的“小魚式”段子結尾,也是他在社交媒體上最“出圈”的一段話。小魚的爸媽都支持他復讀,他們沒上過高中,對他說:“以后的路我們就不懂了,你更懂,你自己走吧。”村里,同輩人大多高中畢業后進廠打工,他不知道,為什么爸媽這么相信他能考上清北。
第三輪演出分到要以“人際關系”為主題創作的組,他講的是小學遭到校園霸凌的故事,但對這個現象的批評被“包圓”了。他的創作習慣是避免冒犯,線上線下演出都盡可能避免直接表達觀點,專注講故事,“害怕評判別人,害怕被別人討厭”。
這幾輪下來,“我的人格介紹得已經比較全面了,接下來我可能不知道會向觀眾說什么了”,所以,他的創作也陷入瓶頸。
受限于尚淺的人生經歷,大學生演員普遍受到創作素材匱乏和話題單一的困擾。同濟大學學生黃栩發現,學生演員寫得多的是校園段子或家鄉、地域相關的段子。“學生演員很少有校園以外的生活,很難從其他方面獲得大家的共情,不像上班的演員可以講上班、結婚的故事。”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選擇回溯所有人成長經歷里的共同記憶是一種“討巧”的做法。一名脫口秀社團負責人告訴記者,脫口秀創作與個人經歷相關,不一定要困在校園話題,還可以寫情感經歷、童年、家庭。小魚寫高考復讀的段子只用了一周,他寫完就知道“大家應該會喜歡”。
艾斯的很多段子和家庭有關。他的專場本打算起名“棍棒底下出‘孝’子”,吐槽爸爸的嚴苛與固執。最初,段子只有3分鐘長,是在他剛講脫口秀半年的時候寫的,那時與爸爸的關系是“比較困擾的事情,完全沒法跟他和解”。這兩年,他慢慢釋懷,決定把自己從小到大的經歷呈現在專場里,而與爸爸的相處則成了主線。“觀眾完全沉浸在我的氛圍里,感知到我的情緒,也愿意配合我,(我)有很強的成就感。”
那場內測的專場結束10天后,北京的觀眾有很長一段時間沒再遇到過艾斯,他的舞臺切換到家鄉西安。媽媽提出想看一次他的演出,爸爸也跟著來了,這次臺上,他沒再講和爸爸有關的段子,他知道,爸爸對脫口秀的理解是“編故事”,沒想過會講真事。
艾斯爸爸反對他講脫口秀,媽媽一開始覺得“挺有意思”,隨他去做,聽說艾斯想把它發展成副業就有點緊張,但后來發現他在社交媒體上演出口碑不錯,就說“別影響找工作就行”。西安的演出剛結束,媽媽當著一群觀眾的面告訴艾斯,他講得非常好。
1月8日,北京市東城區一家小劇場里,一名北京籍大學生演員在演出后沒有直接下臺,目光看向后排觀眾說:“今天的演出不是(綜藝)節目也不是專場,但是我這輩子最有意義的一次演出。”這是他講了100多次“開放麥”后,父母第一次來看他演出。
“怎么可以沒有喜劇社團”
北大的保安要服務超過4萬名全日制在校生,但常去看趣聽演出的保安,能從人群中認出一名上過演出、段子有趣的博士研究生,這是脫口秀在校園存在的印記。
境內第一家脫口秀俱樂部2009年出現在深圳,3年后,東方衛視《今晚80后脫口秀》開播。如今,看《今晚80后脫口秀》長大的00后陸續接受高等教育,他們讓脫口秀在大學校園里也有了聲量。同濟大學的脫口秀社團濟點喜劇成立于2020年,北大的趣聽、復旦大學的旦口喜劇也在第二年相繼成立。
上海交通大學大一學生趙一麟正在著手創辦一個脫口秀社團,去年被兩檔綜藝節目吸引后,她對脫口秀有了興趣,卻發現學校里沒有相關社團。抱著“交大怎么可以沒有喜劇社團”的心態,她拉著同專業的學姐開始找人、籌備、申請,還去找趣聽、旦口喜劇那些成熟的脫口秀社團“取經”。
趙一麟說,學校閔行校區位置離市中心很遠,學生們去廠牌跑“開放麥”不太方便,現在校內很少有真正喜歡講脫口秀的人,但“哪怕做一個喜劇同好會也行”。學校的晚會很久都沒有語言類節目,但今年的研究生畢業晚會導演找到她,希望能出一個節目。另外,她在社交媒體上發帖征集后,籌備社團的群里有了124人,其中40多人已經和她見面聊過,她對把社團辦起來很有信心。
陳一認為,自我表達重要,而“承辦一個塑造夢想的舞臺”同樣很重要。原本,他苦于缺乏機會和場地,遲遲未能把講脫口秀的計劃付諸實踐。他希望能為那些渴望登臺的同學提供一個自我展示的平臺,同時也為觀眾帶來歡笑,“這無疑是一種雙贏”。
從他所在的校區到南京的各家喜劇劇場,往返通常要坐兩小時的地鐵,陳一索性決定在校內“搭”一個舞臺。上學期結束前,他直接將學校的首場“開放麥”活動開到了食堂,只有兩三名演員和零星觀眾,“食堂噪音大,也沒有氛圍,講得非常爛”。在朋友的幫助下,2月開學后,他終于申請到教室,舉辦了第二次活動。
南京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南大心理中心”)在2024年6月舉辦了學校首屆心理脫口秀大會,吸引了近400名學生,現場座無虛席,走道上都坐滿了人,線上直播間還有2800多人。南大心理中心主任陳昌凱意識到,脫口秀這種形式在校園中有著巨大的潛力。當年9月,南京大學南說喜劇社團成立,它是全國首個由高校心理中心發起的喜劇社團組織,用幽默和笑聲為大學生提供心理支持。

南京大學南說喜劇社團成員。受訪者供圖
在任何地方,喜劇都不是單純的娛樂。社團的學生主理人李溪若覺得,當一件很“喪”的事情變成段子時,即便無法消除焦慮,也能帶來一定的情緒釋放。但“真正敢于站上舞臺的同學還是少數”,對于那些不愿表達的學生來說,成為“貢獻大笑”的觀眾,也是一種舒緩心理壓力的方式。南說喜劇指導老師趙琳認為,雖然喜劇無法替代專業心理咨詢,但它提供了一個自我探索與調適的途徑。在輕松的氛圍中,同學們更容易打開心扉,找到共鳴與支持。
趙琳透露,從實際反饋來看,這是最受學生們歡迎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之一。每次“開放麥”的報名鏈接一經發布,幾分鐘內便被搶光。目前,南大心理中心已經舉辦了兩場400人規模的脫口秀大會,社團每周五定期舉行的“開放麥”活動,累計開展了約20次。
學校里,曾有一陣笑聲因他們而起
成立一個脫口秀社團,將脫口秀從個人行為上升到團隊行為,幽默絕不是它的全部,而是需要穩定的練習、嚴密的分工、長遠的規劃,更重要的是,需要更多人投入熱情。
黃栩大一上過一門主持選修課,老師要求課程中期匯報時要在課堂上講一次脫口秀,他因此認識了濟點喜劇的社團成員,后來也加入了社團。最早一批成員創立社團時想,大學要有績點,也要有喜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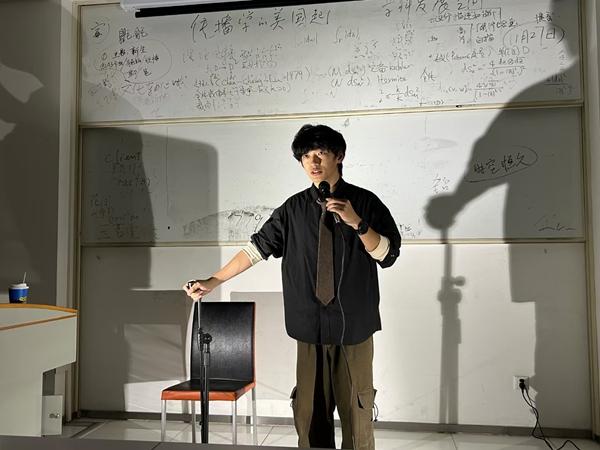
黃栩在同濟大學脫口秀社團濟點喜劇演出,舞臺就是講臺。受訪者供圖
2022年,前輩們相繼畢業,社團有點“青黃不接”,也沒有好的學生演員帶著大家講“開放麥”、辦演出,黃栩自己的脫口秀演出也停滯了。直到2024年,新入學的一名成員很有熱情,挑起社團事務,把濟點喜劇“重新搞起來”。
對于他們來說,校園里能保留好一支麥克風、一個劇場很重要。黃栩認為,上海的成名演員享受很好的資源,“開放麥”、商演都爭相邀請;但對于新人來說,生存空間就變小了,學生演員們因此“缺少在校外鍛煉的機會”。
趣聽的一位創始人也注意到這個問題。畢業后,她沿用趣聽這個名字創辦了一個脫口秀廠牌,希望能給大學生更多登臺機會。不過,小魚坦言,脫口秀廠牌不敢讓大學生上臺演很正常,“很少有大學生愿意花時間來打磨(段子),其他演員練了一年兩年,你在校內講幾場就讓你來演,對觀眾也不負責”。因此,校外的趣聽喜劇在運營得更加成熟的同時,上臺演員的情況也和其他廠牌趨同。
近日,在一場由脫口秀社團舉辦的校園演出結束后,活動負責人在現場告訴記者,他們每次社團招新能招到50人以上,但真正能上臺演出的只有幾個人,社團尊重個人意愿,不會強制。他們每屆在“積累”演員的同時,也要想辦法更新觀眾,因為演員們更新段子的頻率不會太高。
在場的演員們有的會跑校外“開放麥”,有的只在校內演出,脫口秀給每個人帶來的影響不盡相同:“讓我更多觀察自己的生活。”“認識了很多和我一樣喜歡喜劇的朋友。”“面對焦慮和無力的瞬間,什么都做不了,但可以‘嘲笑’它。”
對于小魚來說,脫口秀帶給他“能做好一件事”的自信。在他擔任趣聽社長期間,社團經歷了發展最快的階段,也是社團成員最有壓力的時期。小魚只希望,社團最有熱情的那群人畢業后,社團還能夠“活”下來。最近的一次社團演出復盤,艾斯、小魚、謝謝都沒有到場,他們缺席校內“開放麥”之后,觀眾沒有減少,口碑也沒變差,艾斯覺得“應該能夠平穩交接了”。
至少,社團的意義還在此時此地發生。一場演出結束時,一名趣聽學生演員在社交媒體上寫道:“總要在北大留下點什么吧……或許再過幾年畢業,我們會忘記書本上的知識,忘記食堂飯菜的味道,甚至忘記彼此的名字,但我們會記得,九一劇場曾有一陣笑聲因我們而起。”
(應受訪者要求,陳一、孟軒為化名)

 熱點新聞
熱點新聞
 深度報道
深度報道
 新聞視頻
新聞視頻

 投稿
投稿 APP下載
APP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