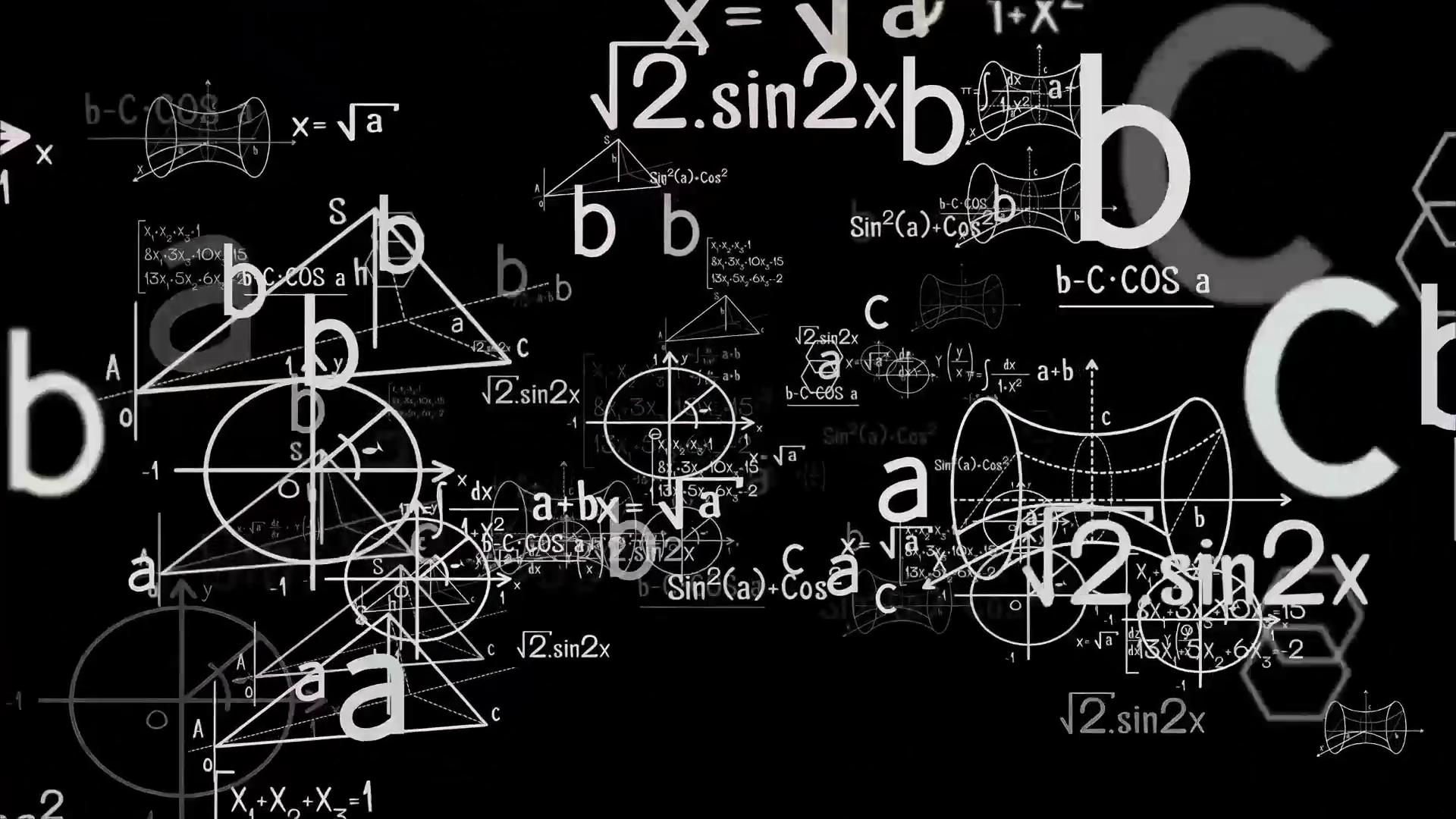西南聯大:教育的燈塔 愛國的豐碑
作者:李東戰
發布時間:2025-01-21 09:51:53 來源:陜西教育·綜合
暑假之際,我懷揣著無盡的敬仰與向往,瞻仰并參觀了西南聯大博物館。那一刻,我仿佛穿越了時空,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在眼前徐徐展開。西南聯大的師生們在艱苦卓絕的歲月里鑄就了無數輝煌偉業。他們用知識與汗水書寫了一部關于責任、擔當與民族復興的壯麗篇章;用自己的行動和生命,書寫了一部感人至深的愛國主義史詩。
在抗日戰爭時期,平津陷落后,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南遷長沙,共同組成長沙臨時大學。隨著戰事的推進,1938年2月中旬,長沙臨時大學又分三路西遷昆明,4月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由于昆明校舍緊張,又在蒙自創辦了一個辦學時間不長的分校。由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組成西南聯大常委會,輪流擔任主席,后因蔣夢麟、張伯苓均在重慶任職,只有年齡最小的梅貽琦長居昆明實際主持校務。西南聯大前后共經歷了8年零11個月,既保存了戰爭年代重要的科研力量,又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蜚聲中外的優秀人才,使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火種薪火相傳,其成就彪炳史冊。
西南聯大(包括附中、附小)的校友中,共有170余人當選“兩院”院士;楊振寧、李政道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黃昆、劉東生、葉篤正、吳征鎰、鄭哲敏5人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鄧稼先、趙九章、郭永懷等8人獲“兩彈一星”功勛獎,又培養了100多位人文大師。然而,誰能想到這樣舉世矚目的成就,竟然是在烽火連天、動蕩離亂的極端艱苦的歲月里取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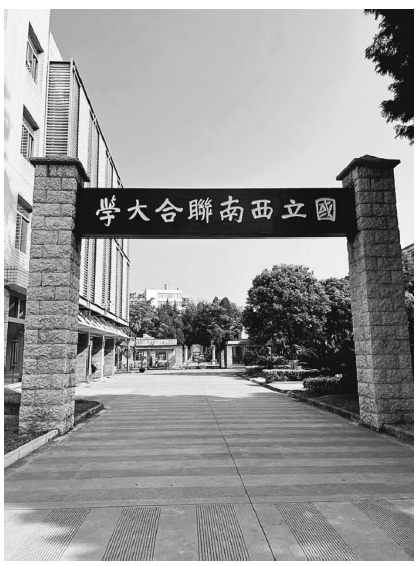
回首往昔,張伯苓校長的“愛國三問”,如同晨鐘暮鼓,讓人振聾發聵。“你是中國人嗎?你愛中國嗎?你愿意中國好嗎?”這三個簡單卻又深刻的問題,如同三面鏡子,映照出學生們內心深處的家國情懷和責任擔當。西南聯大的師生們,在那個戰火紛飛、艱苦卓絕的年代,面對重重困難與挑戰,他們毅然前行,用超凡的智慧與寶貴的生命,生動地詮釋了中華民族堅韌不拔的民族氣節,高揚了聯大人光輝璀璨的愛國主義精神,其事跡令人敬仰,其精神永載史冊。
“九一八”事變后,在大洋彼岸留學并即將學成的趙忠堯義憤填膺,他謝絕了導師的挽留,毅然決然地回到祖國,并利用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的盧瑟福博士贈送的50毫克放射鐳,開設了中國第一個核物理課程,主持建立中國第一個核物理實驗室。北平陷落后,他又冒著生命危險潛回已經封閉了的清華大學實驗室取出這50毫克鐳,把它裝在一個破壇子里,喬裝成難民,成功地把這點兒寶貝帶往昆明,為中國高能物理發展作出了特殊貢獻。1941年,正是中國抗戰最艱難的時期,陳寅恪結束了自己在英國牛津大學的聘任,謝絕了西方學界的一再挽留,毅然回國與同胞共赴國難。王竹溪、張文裕等人亦是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還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王希季毅然放棄即將獲得的博士學位,與鄧稼先、趙忠堯、華羅庚、黃宏嘉、黃昆、唐敖慶等聯大學子一起謝絕了西方國家的優厚待遇,投入新中國的懷抱,在“兩彈一星”等多領域為祖國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貢獻,挺起了中華民族的脊梁。正如華羅庚在歸國途中寫下的那句話:“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是有自己的祖國的。”新中國成立以后,錢三強、鄧稼先、王淦昌、朱光亞、郭永懷等聯大學子響應黨和國家號召,打起背包就出發,隱姓埋名,投身茫茫戈壁,為中華民族的偉大事業默默奉獻著。1964年10月16日,一聲巨響,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羅布泊上空成功爆炸,從此改變了新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歷程中,聯大的師生們響應黨的號召自力更生、攻堅克難,填補了一項又一項重大的科技空白,為新中國的獨立自強作出了巨大貢獻。特別是鄧稼先和郭永懷,他們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祖國和人民。一位女作家曾把鄧稼先比作鑄劍人的女兒莫邪,當莫邪跳進燃著熊熊大火的熔爐中,寶劍得到“人”的祭獻,成為千古名劍。郭永懷亦是用生命為國鑄劍之人。1968年12月5日,郭永懷在實驗中發現了一條重要的數據線索,這一數據能使我國在熱核武器發射領域獲得突破性進展。他當即決定連夜搭乘飛機進京匯報。就在飛機即將著陸時,不幸發生了墜毀事故,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用自己的軀體緊緊護住裝有核彈資料的文件箱,大火燒焦了他的身體,核彈資料完好無損。22天后,依據他用生命保護的重要資料,我國第一顆熱核導彈試爆成功。
“一個民族要有自己的防身寶劍,正義之劍,這把劍就是用報國志士的生命鑄就的。”鄧稼先、郭永懷他們就是為這個民族而生的志士。十年飲冰,難涼熱血。聯大人對新中國這片熱土深沉的愛,讓自己的民族、同胞不再受列強欺凌的責任和擔當讓人感動。正如沈從文先生在《云南看云》里寫的:“戰爭背后還有個莊嚴偉大的理想,不僅是我們要發展,要生存,還要為后人設想,使他們活在這片土地上更好一點,更像人一點!”
西南聯大師生為學術、為事業而拼命的精神深深地震撼著當代有良知的人們。費孝通先生評價曾昭掄先生的一段話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沒有這樣的人在那里拼命,一個學科是不可能出來的。現在的學者當個教授好像很容易,他已經不是為了一個學科在那里拼命了,他并不一定清楚這個學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會覺得這個學科比自己穿的鞋更重要。”與聯大人相比,我們現在缺的不是物質上的富裕,缺的正是他們那種“拼命三郎”的奮斗精神。
回顧西南聯大時期,聞一多、華羅庚兩家14口人,在一間只有16平方米的陰濕廂房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多。后來,華羅庚伏案于牛圈的頂棚上面,完成了上百萬字的成名專著《堆壘素數論》。在昆明,日寇飛機轟炸是常事,有一次敵人的飛機把吳大猷夫婦的小茅屋炸塌了半邊,土墻壓碎了他們盛糧食的瓦缸,里面的半缸面粉和泥土碎瓦片混在了一起。生著病的妻子只好每天把混合著泥土的面粉揉成面團,用水反復搓洗,最后用僅剩下的一點兒面筋為上課歸來的丈夫充饑,就這樣支撐了半個多月。這就是培養了3個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的偉大博士的生活。教授們是這樣,學生們的情況更可想而知,往往幾個人合用一本教科書,缺衣少食更不用說。
鄧稼先在聯大學習時靠姐夫鄭華熾接濟,由于飯量大,一家人節省的口糧根本不夠鄧稼先吃,他只好利用課余時間給人送報紙、當電燈匠打工掙錢,勤工儉學。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地質學女院士郝詒純靠給別人洗衣服、當保姆、刻蠟版掙錢,最終完成了在聯大的7年學業。跑警報,泡茶館,吃夾有砂粒、稗子和老鼠屎的“八寶飯”是當年聯大生活的標志性寫照。教授們一邊跑警報,一邊給學生們講課,學生們在圖書館搶不到座位,就去街道的茶館里寫論文、做試卷。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錢穆寫出了《國史大綱》,湯用彤寫完了《中國佛教史》,馮友蘭完成了《貞元六書》,吳大猷寫出了《多原子分子結構及其振動光譜》,等等。上世紀40年代初,林語堂在昆明看到聯大的狀況后說:“聯大師生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聯大人這種剛毅堅卓、不屈不撓、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不由得使我想到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延安精神。延安時期,同樣也是物資相當匱乏,物質條件異常艱苦,但到處都能聽到革命戰士、熱血青年嘹亮的歌聲,到處都是理想高揚、激情燃燒。正是因為聯大師生們堅守著這種精神,才能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創造出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跡。現在,我們大學的實驗室越來越寬敞,設備越來越齊全,完全有能力、有條件攻堅“卡脖子”的技術難題,為實現偉大中國夢而奮斗,進而創造屬于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貢獻。
“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自古以來,中國人就信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將國家的命運與自己的命運緊密相連。西南聯大師生們的事跡,是愛國主義精神的生動寫照。在那烽火連天、困頓不堪的歲月里,他們以無畏之姿堅守著對祖國的無限熱愛,對知識的執著追求,以及對民族復興的堅定信念。他們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黑暗的時代,更為后人樹立了不朽的榜樣。這份精神力量,跨越時空的界限,依然在新時代熠熠生輝。
作者單位:陜西省咸陽市三原縣教育局


 投稿
投稿 APP下載
APP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