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堅定的政治信仰和崇高的社會理想
作者:郭東軍
發布時間:2021-12-21 10:33:02 來源:陜西教育報刊社
“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
——毛澤東
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勇立時代發展潮頭,歷盡無數艱難險阻,創造了震驚世界的輝煌奇跡,使中國社會一步步走出歷史低谷,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縱觀百年輝煌歷程,中國共產黨攻堅克難、不斷開拓創新的動力本源就是堅定的政治信仰和崇高的社會理想。“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在歷史長河的大浪淘沙中,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拯救國家羸弱的政治信仰,選擇了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社會理想和奮斗目標。為了馬克思主義信仰,為了科學社會主義真理,為了國家繁榮富強,多少共產黨人前仆后繼、拋家棄子,奉獻了自己的血汗、青春甚至生命,在民族振興的征途中留下了永不消逝的浪花。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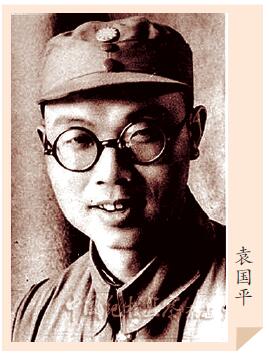
袁國平,湖南邵東人,參加過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廣州起義,歷經長征到達陜北。他認為,一切工作的積極性、犧牲的精神、作戰的勇氣、艱苦耐勞的品質建立在堅定的信仰之上,建立在偉大的理想之上。參加革命之初,他就立下了“愿為中華民族之生存捐軀疆場、死而無憾”的志向,立下了“愿以最后一滴血貢獻于國家民族”的誓言。在“四·一二”大屠殺的白色恐怖中,他毅然決然地堅守了共產主義的信仰,并寄給母親一張照片,背面寫下“此行也愿拋熱血頭顱,戰死沙場,以博一快。他日,兒若成仁取義,以此照為死別之紀念。若凱旋生還,異日與阿母重逢,再睹此像,再談此語,其快樂更當何如耶!”這充分彰顯了他堅如磐石的革命信仰。
長征前,袁國平把大女兒送到了岳母家,交由妻姐撫養,但大女兒13歲時被送給別人當了童養媳。由老母親照料的二女兒,在貧寒困苦中夭折。八個月大的兒子也被送回了湖南老家。袁國平犧牲后,其母親傷心過度,哭瞎了雙眼,年幼的小兒子牽著雙目失明的奶奶沿街乞討,要飯度日。面對家境的極度貧困,袁國平在家書中這樣寫道:“此刻我身無分文,無法幫助家里,因為我們是以殉道者的精神為革命、為國家和民族服務的。或許有人要說,我們是太不聰明了,然而世界上應該有一些像我們這種不聰明的人。請家里不要想將來生活怎么辦,因為中國正在大的變動之中,中國抗戰成功,不愁無飯吃;抗戰不幸失敗,則大家都要當亡國奴。”
在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中,面對軍長葉挺被扣押,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遇難的情況,時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的袁國平在極度危急時刻挺身而出,指揮剩余部隊繼續突圍北撤。在激烈的戰斗中,袁國平身中數彈,倒在血泊之中。當他被戰友們發現時,血肉模糊,不能行走,他要求大家趕快走,不要管他。戰士們不肯丟下自己的首長,堅持用樹枝扎成的擔架抬著他走。密集的子彈呼嘯而來,抬擔架的戰士相繼倒下,袁國平掙扎著對身邊戰士們說:“你們趕快突圍,不要管我了!出去一個是一個,否則一個都出不去。”他掏出一個筆記本和七塊大洋,讓戰士們替他交黨費。乘人不備,袁國平摸出手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扣動了扳機。戰士們震驚了,他用行動兌現了自己的諾言:“如果我們有100發子彈,要有99發射向敵人,最后1發留給自己,決不當俘虜。”為了不當俘虜,為了不拖累戰友,為了心中的信仰,時年35歲的袁國平將寶貴的生命獻給了中國革命事業,實現了他“舍身赴敵、戰死沙場”的夙愿。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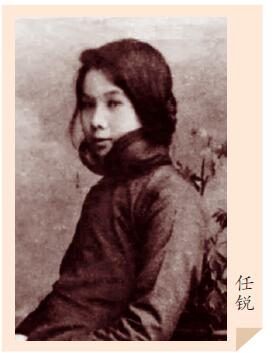
任銳,河南新蔡人,少女時代投身革命加入同盟會和“鐵血團”,后加入中國共產黨,其志同道合的丈夫孫炳文在“四·一二”大屠殺中被捕入獄,面對威逼利誘和嚴刑拷打,孫炳文守口如瓶,嚴守黨的秘密,慘死獄中,表現出共產黨員視死如歸的崇高品德和堅守信仰的鋼鐵意志。在白色恐怖中,任銳帶著子女輾轉于四川、安徽、江蘇、湖北、河南、北京等地,在近十年的顛沛流離中,艱難地尋找著黨組織。其間,迫于生計和工作需要,她把最小的女兒送給了姐姐。歷經千辛萬苦,任銳終于與組織取得了聯系,服從組織安排。
在延安,她先后在抗大和馬列學院學習,因為經常關心、幫助、愛護年輕學員,被學員親切地稱為“媽媽同志”。在重慶璧山第五保育院工作期間,任銳對保育院里500多個饑寒交迫、死里逃生的孤兒,視如己出,精心呵護。對患病的孩子,她專門編隊,親自護理,悉心照料;用自己牙縫里摳下的生活費給孩子們買雞蛋、餅干、水果,補充孩子們的營養;夜晚來臨,給孩子們講述革命故事,孩子們親切地稱她“任銳媽媽”。在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監印期間,她高度負責,盡職盡責,精益求精,一絲不茍,反復斟酌校訂,工作中基本沒有差錯。
在大生產運動中,52歲的任銳不顧年邁體弱,率先垂范、以身作則,無論紡線、喂豬,還是種瓜,“媽媽同志”不甘人后,任務樣樣超額完成。閑暇之余,為小戰士縫補衣服,講革命故事、人生道理。組織上每個月發給她的生活補助,她自己從來不用,總是省下來送給有小孩的家庭和體弱的同志;衣服補了又補,把新發的制服一次次給退回去,留給前方戰士。
1945年秋天,組織上考慮她為革命奔波了大半生,體弱多病,便把她失散多年的小兒子從前線調回,留在延安工作,以便照顧她的生活,但她果斷拒絕,堅持送兒子上戰場,并賦詩《送兒上前線》,勉勵兒子秉承父志、沖鋒陷陣、報效國家:“送兒上前線,氣壯情正愴。五齡父罹難,家貧缺衣糧。十四入行伍,母心常凄傷。烽火遍華夏,音信兩渺茫。昔別兒尚幼,猶著童子裝。今日兒歸來,長成父模樣。相見淚沾襟,往事安難忘?父志兒能繼,辭母上前方。”就在革命即將勝利的1949年4月,任銳積勞成疾、百病纏身,懷著對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的無限憧憬,懷著對追求一生的美好事業的無限眷戀,閉上了雙眼。善良的人們沒忍心告訴她,被她執意送上前線的最小的兒子孫名世,數月前已經犧牲在遼沈戰場。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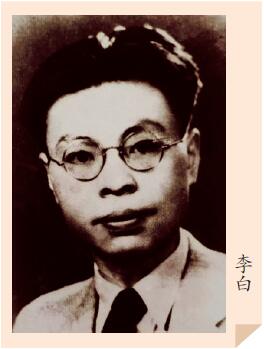
《永不消逝的電波》中李俠的人物原型李白,湖南瀏陽人,1925年參加革命。我黨建立無線電學習班時,李白被調入學習班學習。憑借著對黨和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李白“學習上不知疲倦”,早起晚睡,潛心研習,不僅熟練地掌握了電臺使用方面的專業技能,還熟練地掌握了英文和打字,并擔任紅五軍團十三軍無線電隊政委,在歷次反“圍剿”斗爭中,電臺聯絡順暢,屢立戰功。長征中,李白背著電臺,多次用身體保護電臺,保障了通訊聯絡的暢通與準確及時,他始終認為電臺重于生命。
抗戰爆發后,組織需要李白到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淪陷區——上海,設置秘密電臺,李白堅定地回答:“我的一切都是屬于黨的,黨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只要我的工作對黨有益,對人民有利,不管有什么困難,我一定努力去克服。”1937年10月,經黨組織安排,李白化名李俠,住進了貝勒路148號3樓一間十分簡陋的小閣樓里。在軍、警、特務橫行的上海,在電信器材非常有限的條件下,李白通過多種渠道一點一滴地積累組裝電臺的零部件。經過半年的努力,李白組建起秘密電臺,架起了延安與上海之間的“空中橋梁”。黨中央的一項項指示及時傳達到上海,一份份珍貴的情報也總能及時地傳到延安。解放戰爭期間,從安全保護的角度出發,黨組織有意將李白調回延安,但從工作角度,沒有人比他更適合留在上海,因此當組織征求他的意見時,李白毫不猶豫地表示:“黨需要我留在上海,我絕對服從!”
在國民黨特務密布、警車橫行的上海,李白的工作艱苦且危險。他把電臺安置在一個小閣樓上,夜深人靜時就開始工作,憑著對黨的無比忠誠、堅定的革命意志和精湛的業務能力,機智地與敵周旋,不管嚴冬,還是酷暑,他都能出色地將地下組織搜集的各種情報,通過電波傳送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區。李白自己組裝的電臺功率很小,天線又不能外露,經過刻苦試驗和不斷摸索,他能夠把100多瓦的電臺改裝到十多瓦,并始終清晰地把信息發到千里之外的延安。新中國成立后,當蘇聯情報電訊專家得知這一情況時,對他的技術水平和能力大為驚嘆。李白白天破譯電文,晚上收發電報,工作十分辛勞。他工作的閣樓又悶又熱,由于是秘密收發電報,還得把窗戶關得嚴嚴實實。收發電報的時間定在夜間零點到四點,每次都要堅持好幾個小時。夏季,當妻子進去幫他收拾東西時,常常會發現閣樓的地板上有他滴下的大量汗水,但是李白總是愉快地說:“只要工作順利,我的心就很涼爽,天熱也就被忘掉了。”電報多的時候,工作要延長到天亮,他在暗室里常常察覺不到,延安總部電臺的戰友總要親切地提醒他:“李白同志,天已微明,再見!”
1948年12月29日晚,當李白緊張工作時,他的住地突然被百名軍警包圍。當時他完全有機會脫離危險,但是當天的情報太重要了——國民黨軍的“長江防御計劃”。因此他完全不顧個人安危,飛速按動電鍵,在敵人的槍口下完成了最后的發報任務。李白第三次被捕。敵人對他動用了各種刑具,一連折磨了30多個小時,李白口鼻流血,昏死過去好幾回,但他毫不動搖,拒不招供。李白在獄中受盡折磨,堅貞不屈,保守了黨的重大機密,使黨的預備電臺繼續保持同黨中央的聯系,電波沒有中斷和消逝,直至上海解放。面對來探監的妻子,李白從容地說:“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不論生死,我心里都坦然,你們可以和全國人民一樣,過和平幸福的日子。”當天晚上,年僅39歲的李白被秘密殺害。20天后,上海解放。李白從事秘密工作12年,為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勝利立下了不朽功勛,成為黨和人民軍隊歷史上傳奇的諜報人員。
信仰,是夜晚漆黑大海上的燈塔,是風雨之中迷路者的方向。苦苦尋求民族出路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旦將馬克思主義視為堅定的政治信仰,就會將建立共產主義社會樹立為神圣而高遠的社會理想,就會將之轉化為改造舊中國、創造新世界的力量,就會掀起社會革命的滾滾洪流。
一代知識分子,為了堅定的政治信仰和高遠的社會理想,在山河破碎、硝煙滾滾的抗戰時期,背井離鄉,克服重重困難,沖破艱難險阻,歷盡千辛萬苦,到達延安。“打斷骨頭連著筋,扒了皮肉還有心,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爬到延安城。”印度援華醫療隊隊長愛德華在乘車去延安的路上,總是在崎嶇的山路上,總是在凌冽的風雪中,看到一個個衣衫襤褸的年輕人徒步而行,奔向延安,不由自主地發出這樣的感嘆:“奇跡,奇跡,這簡直就是奇跡!”西安到延安大約800里,道路崎嶇,主要靠步行。張道時曾回憶:“步行800里,說說容易,真走起來,才知并不簡單。每到宿營地,一踏進兵站,大家就一頭躺在地鋪上,再也不想動彈了。渾身骨頭像散了架,腰酸腿痛、脖子發硬、喉嚨冒火,手和腳都腫了起來。”國民黨當局為了阻止革命青年奔赴延安,沿途設立層層封鎖線,特務盯梢,將抓到的青年學生送到“三青團招待所”和“戰干四團”,威逼利誘,酷刑摧殘。著名作家魏巍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三次被敵人抓住關押,每次又都設法逃了出來。播音員蕭巖,在和姐姐路巖去延安的途中被國民黨攔截扣押,她們不屈不撓,終于在共產黨的斡旋下獲釋,不改初心奔赴圣地。音樂家賀綠汀為了去延安,攜妻小,改名換姓,仍被國民黨抓捕并送回,后經周恩來斡旋,歷經曲折,才到達延安。據《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記載:“1938年夏秋之間奔向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說是絡繹不絕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達延安。”任弼時在1943年12月底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指出:“抗戰后來到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4萬余人。”
共產黨人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這種“特殊材料”就是堅定的政治信仰和崇高的社會理想:為了人民幸福安康,為了國家繁榮富強,為了真理,奉獻智慧和生命。
(作者系延安大學澤東干部學院副院長)


 投稿
投稿 APP下載
APP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