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大校史上的幾位“國”字號人物
作者:千里青
發布時間:2021-04-02 15:18:17 來源:陜西教育報刊社

一、“國師”黎錦熙
“國師”是一個古舊的稱謂,這里姑且用之。黎錦熙早年在長沙第一師范擔任歷史教員時,毛澤東是他的學生。毛澤東后來成為國家主席,不忘舊緣,仍尊黎錦熙為“我的老師”。因此,我們稱黎錦熙為“國師”。
黎錦熙,字邵西,湖南湘潭人,1890年2月出生,僅比毛澤東年長三歲多。他畢業于清末湖南優級師范學堂史地部,一生從事文史教育和國語統一事業,著述甚豐。1931年任北師大文學院院長,抗戰爆發后隨北師大遷來西安,后至陜南城固,執教于西安臨大、西北聯大、西大,曾任國文系主任。
黎錦熙與毛澤東交往密切,常通音信,并一直甘冒風險保存著毛澤東寫給他的信件。1939年,毛澤東得知他在城固,曾從延安寄贈新著《論持久戰》一書給他。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接見馬師儒(時任西大文學院院長,后任校長)時,曾囑托馬師儒:“返陜南后,請代我問候我的老師黎邵西先生。”
黎錦熙是無黨派人士,一貫堅持進步立場。1939年在西大時,國民黨區分部曾動員他入黨,他堅決拒絕,將申請表擲于廢紙簍中。為此區黨部向來校視察的教育部次長說他的壞話,要求解聘他,因他資格老而未敢輕動。他常對人說:“一般人都說什么反動學生,我看他們功課都很好,相反地黨團員則功課都不好。”一般人說的“反動學生”即地下共產黨員、進步學生,他所說的“黨團員”指國民黨員、三青團員。現存檔案有當時西大中共地下組織向省委的匯報材料,稱黎錦熙“對共無成見,不頑固”。黎錦熙為西北聯大撰寫的校歌歌詞保留至今,他還以歌詞為綱,寫了一部簡明的西大校史,最先把西大校史溯源至晚清。
解放前一年,黎錦熙返回北師大,仍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1949年6月北京解放不久,毛澤東就親臨北師大看望他,一見面就喊“黎老師”。此后,毛澤東曾多次接黎錦熙到中南海敘談,師生之間,情意綿長。
黎錦熙于1978年3月謝世,終年88歲。

二、“國史”侯外廬
“國史”一詞或指一國之史、一朝之史,或指古代的史官。現代不設史官之職,卻有研究歷史的專家。侯外廬作為史學泰斗、中國思想史方面的絕對權威,稱他為“國史”似不為過。
解放初期,侯外廬主持西大校政,大刀闊斧,高屋建瓴,政績突出,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無須贅言。這里單從“國史”的角度,略述他的卓越成就和杰出貢獻。侯校長在史學領域耕耘半個多世紀,他對上下幾千年的中國社會史和思想史都有系統的研究,著作宏富,見解獨到,自成體系,是我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開拓者。論者以為,他的治史生涯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早期(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為發軔期。代表作有《中國古代社會與孔子》《中國古典社會論》《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船山學案》等,這期間他接受周恩來的建議,撰寫了80萬言的《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二、中期(40年代后至60年代初)為發展成熟期。個人著作有《三民主義與民主主義》《中國古代社會史》《孫中山到毛澤東》《漢代社會史緒論》《社會發展史的一些問題》《中國哲學史略》《中國歷代大同理想》等,這期間他聯絡杜國庠、趙紀彬、邱漢生等老專家和一些青年學者,主持完成了一項“大工程”——260萬言的五卷本巨著《中國思想通史》,這標志著“侯外廬學派”的形成,表明他在史學研究領域登上了一個無人比肩的高峰。三、晚期(70年代中至80年代中)為繼續開拓總結期。著作有《中國近代哲學史》《中國封建社會史論》《中國思想史綱》(上下冊)等,特別是他和邱漢生、張豈之合著的130萬言的《宋明理學史》(上下卷),填補了解放以來我國史學研究中的一項空白。
一代“國史”侯外廬于1987年9月謝世,終年84歲。他的遺愿是寫一部100萬言的《中國思想通史補編》和一部更完整的《中國近代思想史》。這個遺愿有待侯氏學派第二代、第三代去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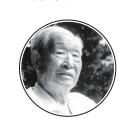
三、“國手”王耀東
體育界把國家隊選手稱為“國手”,足球國家隊成員又稱“國腳”。1921年5月,二十剛出頭的王耀東經過層層選拔進入國家籃球隊,作為主力隊員參加了第五屆遠東運動會,贏得了籃球比賽的金牌。他是名副其實的老“國手”。
王耀東畢業于北師大體育專修科,后執教于北平大學,抗戰之初來西安,歷經西安臨大、西北聯大、西大各個時期,直到2007年以107歲高齡辭世,在西大整整工作了70個年頭,為西大的體育教學傾注了畢生的精力。生前學校曾破例決定他為永不退休的終身教授。
耄耋之年的王耀東曾擔任全國體育總會副主席。他是中華民族近百年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人,也是中國近百年體育發展史的參與者和見證人。1999年9月,西大為這位中國體壇世紀老人舉行了百歲華誕暨執教80周年慶賀大會,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伍紹祖等親臨西大向王老祝賀,同時還宣布設立“王耀東獎學基金”,舉行了《王耀東傳》首發式。
2002年10月,西大百年校慶大會隆重舉行,102歲的王耀東登臺講話,思維清晰,聲音洪亮。他以自身的健康長壽有力地證明了“生命在于運動”這句至理名言。

四、“國嘴”齊越
國家大事,重大新聞,通過他的嘴、他的聲音傳播出去,故曰“國嘴”,齊越當之無愧。
齊越,原名齊斌濡,河北高陽人。1942年來到城固,就讀于西大外文系,學習俄文專業。他政治上追求進步,在校地下入黨,積極投身學生運動,學習刻苦勤奮,專業成績優異,在課外活動中充分表現出朗誦和講演的才能。
1946年4月,西大發生震驚全國的學潮,齊越被誣為“暴徒”受到反動當局搜捕,在他的河北同鄉、數學系魏庚人老師掩護下成功脫逃,進入華北解放區,不久調到陜北新華廣播電臺,擔任播音員,這正是他的專長。他是新華臺唯一的男播音員。當解放戰爭進入決戰時刻,人民軍隊摧枯拉朽,勢如破竹,我黨我軍的許多重要文告和新聞,都是通過齊越之口廣播出去,傳遍全中國、全世界的。當時新華臺的女播音員錢家楣后來回憶說:“那時齊越一接到前線捷報,就高高舉起,在院子里邊跑邊喊,把機務員都逗笑了,指著他:瞧,齊越!他當即就充滿激情地把捷報播出去了。”
齊越播音生涯中最可圈可點的經歷,就是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擔任開國大典的播音員。從此,他長期堅守中央廣播電臺主播崗位,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嘴”,播音界同行則稱他為“老頭子”。他的一系列經典播音,人們記憶猶新。1975年齊越調任北京廣播學院教授,是我國第一位播音學教授。1980年齊越再次出現在萬眾矚目的場合,為公審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宣讀證詞,似乎只有他最能發出義正詞嚴的聲音。“北廣”現稱中國傳媒大學,一直奉齊越為宗師,塑立雕像,頂禮膜拜。為弘揚齊越精神,還設立了齊越朗誦藝術節,已辦了十多屆。
1993年11月,齊越病故,享年71歲,新華社發了專電,給予高度評價。

五、“國使”申健
“國使”者,國家派出的使節也。申健早在中印建交之初就擔任首任駐印度臨時代辦,隨后又擔任首任駐古巴大使,1980年又出任駐印度特命全權大使,是一位資深的“國使”。
申健,原名申振民,化名陳松嚴,1937年至1939年在西大法商學院學習,1938年在校入黨。他在西大雖只有短短三年,卻經歷了西大三變其名(臨大、聯大、西大)的全過程,這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出發點。申健入黨后,曾要求去延安,組織上決定他留校從事地下工作。在此期間,他與熊向暉、陳忠經一起打入胡宗南部“臥底”,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憑著大智大勇,出色完成任務,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多次嘉獎,被周恩來副主席譽為我黨隱蔽戰線“后三杰”(前三杰為李克農、錢壯飛、胡底)。1946年胡宗南派他們三人去美國深造,經請示上級黨組織同意,將計就計,去了美國。后因國內有人被捕暴露了他們,遂斷了經濟來源。他們通過蘇聯駐美使館資助,于1949年7月回國。回國后,三人均肩負重任。申健除多年擔任駐外使節,還做過中聯部副部長,一度主持中聯部工作,是新中國第一代杰出的外交家。
剛從美國回來時,組織上指示他們改名,申振民原改為申建,取獻身新中國建設事業之意,劉少奇主席在一張任命書上給“建”字加了個單人旁,從此就使用“申健”這個名字。
他作為“國使”,頭一個使命是出使印度,過了30年,他的最后一個外交使命,還是出使印度。人所共知,中印關系十分敏感,也十分棘手,一是達賴問題,二是邊界問題,都是涉及國家根本利益的難題。申健堅持原則,掌握政策,注意策略,敢于斗爭,善于斗爭,表現出精湛的斗爭藝術,可謂不辱使命。
“文革”中,忠良遭害,奸佞橫行,工作局面異常艱難,申健受命主持中聯部工作,經受了巨大的壓力,付出了大量心血和精力,使中聯部的工作正常運轉,成為當時唯一對外繼續活動的部門。后任中聯部長耿飚曾特意書寫“難能可貴”四個大字贈給申健。
1987年,申建被推選為西大北京校友會會長。
1992年3月,申健去世,享年77歲。
來源:《西北大學報》第603期,有刪節


 投稿
投稿 APP下載
APP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