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樣的學生發展測評——訪PISA分析部門負責人池田京
作者:馮麗穎
發布時間:2018-12-13 18:03:23 來源:陜西教育新聞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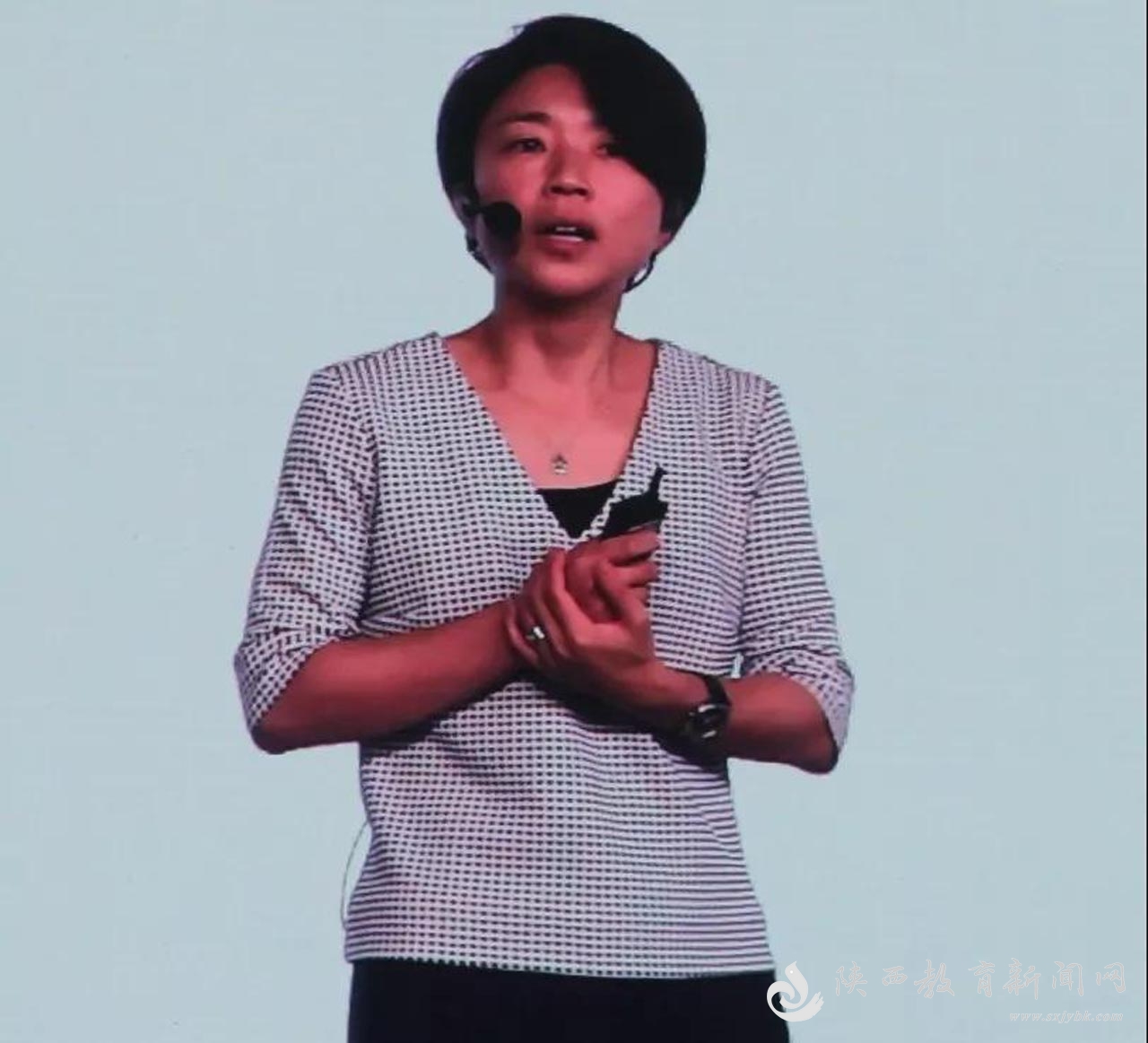
作為國際性學生評估項目,每次的PISA測評結果都備受關注。在第五屆中國教育創新年會上,就PISA測評的內容、科學性等,記者有幸采訪了OECD資深研究員、PISA分析部門負責人池田京女士,特別感謝北京大學博士、前21世紀教育研究院教育創新研究中心主任、創新教育交流會理事、《為生活重塑教育——中國的教育創新》主編馬志娟老師的翻譯。
記者:PISA測評標準或者抽樣方案會不會根據國家和地區作一些調整,如何保證測評結果具有可對比性?
池田京:PISA是一個由經合組織發起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包含了很多指標,除了學業成績外,還有其他一些與學業相關的變量。這樣一個測試使得我們有一個可供國際比較的標準,通常會以經合組織國家平均的分數作為一個參照,這樣就能知道每個國家的學業成績在國際上處于什么樣的位置。
PISA從2000年開始,每三年做一次測試,持續下來,我們使用了同樣的量表,使得我們可以持續地觀察學生學業成績的變化。更重要的是,除了學業成績之外,我們還會搜集其他一些情景的變量,不僅包括學生的,也包括家長和教師的,我們可以通過交叉分析這些數據去研究學業成績與學生家庭背景、社會經濟狀態等各種變量之間的關系,從而幫助政策制定者和教育者去理解影響學生學業成績的因素。
除了測試,還有調查問卷。PISA的問卷會收集學生家庭背景、對學校的態度、生活質量、學習動機等問題。我們也會收集來自校長、教師、家長以及一些機構領導人的問卷,有一部分是可選的。
PISA的評估對象是15周歲的學生。因為15周歲通常是一個國家基礎教育的最后一年,我們想要知道,這些學生在經過了義務教育之后,多大程度上準備好了去工作,或是繼續升學。
記者:中國學生15周歲的這個時間并不是基礎教育的最后一年,在上高一,那么測試的數據和國際比較的標準相比,是科學的嗎?
池田京:抽樣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按年齡來抽樣,一種是按照年級來抽樣。按照年級來抽樣的話,實際上是按照特定的那個年級段所學的課程來抽樣的。我覺得這個不公平,因為每個國家在特定的年級段,內容是不一樣的。PISA以年齡來劃分,是指在特定的年齡段,學生掌握的知識和運用的情況,就可以消除掉不同國家在課程方面的差異。日本也是一樣的,15歲的孩子在上高一。實際上,我們也看了按年齡段分的結果,通過技術可以把按年齡段的那個抽樣最后還原到學生在特定年級的成績。我覺得,只要是15歲,九年級和十年級并沒有差別,但是個別的國家,比如法國和比利時會有差別。因為他們有比較多的成績低的學生,這里面有比較多的復讀學生,就是九年級讀了兩年,這個會干擾整個數據的測試結果。
記者:在您演講中提到,PISA測評主要測試閱讀、數學和科學。同時,每隔3年,會增加一個新的測試元素,2012年測試了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2015年增加了合作解決問題的評估。2018年新增全球素養評估,2030年計劃加入創造性思維的評估。全球素養從哪些方面進行測評?合作能力又是怎么測評的?
池田京:在全球素養測試里包括認知和非認知兩個方面:在認知方面一方面是觀點、立場,另一方面是批判性思維;在非認知方面,主要看態度,比如對移民、其他文化持一個什么樣的態度,學校是否鼓勵學生接納這個多元文化等。
合作能力是電腦生成的一個虛擬場景,學生在線和電腦生成的具體的人物角色合作解決問題。我們做過一個前測,人機交互的測試方式測試的學生水平是很穩定的,不需要找真實的學生來扮演合作伙伴來測評。未來技術更成熟的話,人跟人通過計算機交互來體現他們的協作能力,當然這需要時間。
記者:中國北京、上海、江蘇、廣東四地參加了PISA測評,PISA測評結果顯示,這四個地方學生學業成績在平均分以上,但是校外學習時間最長,可能是什么原因導致的?
池田京:這個問題可能你比我更清楚,課后時間長,是不是存在很多“影子學校”(培訓機構)。我來自日本,日本其實也一樣。因為競爭很激烈,如果別人學自己不學,就會落在起跑線上,就會被迫加入這個校外培訓。這個問題的確值得反思和重視,花了大量時間在課后學習,就剝奪了他們在其他方面的時間,比如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時間。我們現在更加重視學生的生活質量以及非認知方面的情況。
記者:中國其他地區和學校若要參加測評的話,如何才能加入?測試的費用包括哪些?
池田京:這四個地方參加測評是中國政府決定的,我們借助技術工具去抽樣,先抽出學校樣本,再抽出學生樣本。我們也有對學校單獨測評的項目。
所有的費用是由參與的國家來承擔,支付的費用包括專家組做抽樣、出問卷的費用,當地實施抽樣調查的費用,問卷翻譯的費用,開放性問卷的編碼費用。
記者:PISA測評結果顯示,日本學生的學業成績也是比較好的,有什么好的教學方法可以借鑒呢?
池田京:日本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成績也比較好,可能是日本學生整體的成績比較好。但是從調查來看,學生并不喜歡學數學,也不喜歡閱讀,學生并不感到快樂,所以我不并主張推行這個模式,因為結果可能是好的,但過程很痛苦。不過日本不斷在改進和調整,就是怎么讓學生更快樂地學習。


 投稿
投稿 APP下載
APP下載





























